




許光達筆記寫滿求學干貨
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中,一份字跡工整的課堂筆記詳細記載了炸橋、阻擊等教學內容,如今看來這稱得上學生筆記中的典范。而這份筆記的主人正是黃埔軍校五期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許光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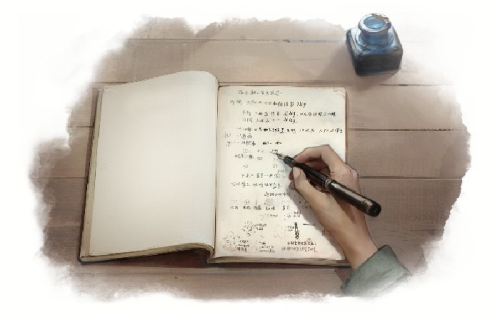
許光達筆記寫滿求學干貨
“寓學于戰,學練結合”是黃埔軍校軍事教育的一大特點。軍校采用新的軍事理論和技術進行講授、訓練,注重理論與實操相結合。
學生訓練刻苦 珠江漲潮操場漫水照樣出操
1926年1月,許光達考入黃埔軍校,經過入伍生訓練后編入第五期炮科。在軍校練習中,他認真刻苦,是全隊的隊列動作標兵;在理論課堂上,他勤奮好學,所做的課堂筆記字跡工整,清晰記載了炸橋、阻擊等軍事課堂內容,是他在軍校的求學實錄。“寓學于戰,學練結合”是黃埔軍校軍事教育的一大特點。訓練、演習交替進行,互為補充,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既通軍事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軍事人才。
建校初期,軍校只有步兵科,課程分為“學科”和“術科”兩大類。“學科”內容有步兵操典、射擊教范、戰術學等軍事理論,旨在讓學生掌握運用一般軍事學的原理。“術科”以制式教練、戰斗教練、野外演習等為主,旨在讓學生掌握各種陣中勤務和技術原則,培養指揮小部隊作戰的能力。
軍校從第二期開始逐步增設了炮兵、工兵、輜重兵、憲兵等科,實行分科教學,課程有公共課和專業課。“戰術”“兵器”“筑城”和“交通地形”被稱為“四大教程”,各自下面又分多個細目。從第三期開始,黃埔軍校實行入伍生制度。入伍生訓練為期三個月,入伍生階段是軍校的預備教育,目的在于教授軍事學的基本原理,讓入伍生恪守紀律,習慣軍營生活及各種勤務,打下戰斗基礎。入伍生期滿要進行考試,合格才能成為正式學生。
學生入學后立即進行制式訓練。首先是單人徒手訓練,學生要學習各種步法、轉法。個人操練熟悉后,進行班訓練和排、連、營訓練。徒手訓練熟悉后,進行持槍訓練,包括托槍、下槍、舉槍、裝槍等,然后還有密集、疏開、散開等隊形訓練。這部分訓練大多在操場上完成,無論是寒冬抑或酷暑,操場上總能見到學生們摸爬滾打的身影。徐向前回憶,“操場緊靠珠江口,漲潮時操場里的水都漫過了腳,照樣要出操。”
野戰相關的訓練內容則主要在野外完成,如挖掩體、目測距離、放步哨以及行軍、宿營、戰斗中的聯絡和協同等。此外,夜間還要進行緊急集合、點火法、方位判斷、戰備行軍等訓練。有一次剛下過雨,地上泥濘不堪,學生們在跑步中進行訓練。忽然值日官高呼“臥倒!”學生隊伍頓時有點慌亂。值日官大聲說道:“口令就是口令,不能猶豫,也不能畏懼。此刻敵人的炮彈在頭上‘吱吱’地飛過來,機槍猛烈朝我們掃射,你們還有時間猶豫嗎?”這一幕,讓不少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中展出了一份《野外演習各種想定》,這是軍校射擊野外演習內容的腳本,其中包括了攻擊、防御、退卻、行軍、駐營、警戒、偵察、聯絡、特種作戰等科目。野外演習常在瘦狗嶺、珠村等地展開,演習過程模擬真實的戰爭場面,將學生分為兩隊,進行激烈對戰,在炮聲隆隆的環境中鍛煉膽量、提高實戰能力。學生畢業前還要參加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嚴格考核,檢驗所學知識技能,評定合格者方能畢業。
除了日常教學,演講也是軍事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分為普通和特別兩種。其中,舉辦特別演講主要是為了介紹軍事上的最新知識,舉辦時間、地點一般都是臨時決定的,全校師生都要到場聽講,比普通演講隆重得多。
軍校校規嚴格 上課坐姿不得歪斜、用餐規定在10分鐘內
軍校的校規極為嚴格,日程安排也很緊張。在寢室里,學生還要遵守《寢室規則》八條。每天早上5點,學生要準時起床、整理內務,把被子疊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塊”,水壺、干糧袋掛在墻上,行距整齊,排成一條水平直線。洗漱完畢出早操跑步,然后再開始一天的學習訓練。
學生在軍校用餐,每餐只有10分鐘的用餐時間。吃飯時,只要一聲哨響,無論吃完與否,學生們都必須放下飯碗站起立正。還有學生被疊被子難倒,因為疊不出“豆腐塊”而滿頭大汗。一些學生入校前從未體驗過如此緊張的節奏,十分不適應。經過一段時間的嚴格訓練后,學生們也逐漸意識到,這是成為一名優秀軍人的必由之路。
黃埔學生中還有“三操二講”之說。“三操”指一天早中晚要出操三次,“二講”則指課堂上課和晚自習。其中,上課時,學生要把軍帽放在課桌左上方,不抄筆記時雙手要放于膝上,坐姿挺直,不能有半點歪斜,雙目注視老師,抄筆記時身體不能扭動。
當時,蕭楚女、高語罕、惲代英等軍校授課老師都是杰出人物,深受學生愛戴。在課堂上,師生們有時也會為學術話題進行一番激烈辯論。陳明仁在軍校上學時常有獨特見解,與老師爭論得面紅耳赤,也因好學態度獲得老師的認可。
時任政治部代主任的熊雄在《告第五期諸同學》中指出:“革命軍唯一的特色,就是有黨紀相范,軍紀相繩,能使每個分子,對于紀律,卻能自覺遵守,自動服從,如此,即所謂革命的紀律,鐵的紀律。否則橫沖直撞,毫無組織,何有紀律?”有一次,有位政治教官起床遲了,教育長專門到其寢室當面批評教育。可見,不僅學生要嚴格遵守軍紀,老師更是如此。
作為一所新型軍校,黃埔軍校注重革除舊式軍閥軍隊的風氣,培養革命軍人,在嚴格訓練之外也不失溫情。軍校學生來自天南海北,其中,來自西南、湘、贛、川等地的學生愛吃辣椒,來自廣東和部分北方地區的學生則怕辣。后來,軍校要求伙食采辦負責人要根據各連隊吃辣椒人數的情況適當搭配辣椒,炒菜時辣味菜要單獨做,讓學生自由選擇。有些體弱的學生一開始長跑時跟不上,教官也采用循序漸進的做法,以此增強他們的體力和意志力。
當時兵器匱乏 葉劍英借槍械、做模型來授課
黃埔軍校在選拔軍事教官時有嚴格規定。創校初期,軍事教官中保定軍校畢業生最多,一至三期就有不少于69位,占比接近80%。此外還有陸軍測量學校、云南講武堂、南洋大學的畢業生。這些教官不僅有扎實的軍事理論,也有一定帶兵經驗。隨著黃埔軍校學生畢業、成長,其中有不少學生充實到教學隊伍中來,實現了“人才鏈”的良性循環。
1924年4月,葉劍英從粵軍調到黃埔軍校擔任教授部副主任。除了高效地完成日常工作,他也兼任軍事教官,先后講授了兵器學課、劈刺課和戰術課三門課程。兵器學是一門深奧的學科,教學中需要借助兵器實物演示。鑒于當時軍校中的兵器十分匱乏,葉劍英只好回到粵軍二師借槍械輔助教學。實在沒有實物時,就動手制作兵器模型和彩色掛圖。此外,他還組織學生到廣州兵器廠、火藥制造廠參觀學習,帶領學生參觀長洲要塞炮臺的火炮,到部隊學習實彈射擊。后來,軍校在軍械方面的緊缺局面才得以緩解。當時,軍校師生對軍械補充的期盼在他們的記述中表露無遺:“第二天早上,全體動員,搬運軍械……搬運的人群如梭般往來不息。‘哼’‘哈’之聲不絕,人人臉上都笑開了花。”
軍校還迎來一批“特殊”的教官——來自蘇聯的顧問。其中,通信顧問科丘別耶夫克服語言障礙,僅用30多分鐘就教會了學生們唱《國際歌》。
 關注 · 廣州政府網
關注 · 廣州政府網